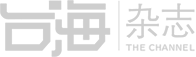讲述/刘宇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 卢燕

2005年1月22日,在泰国普吉岛的海边,来自喀麦隆的爱莎呼唤女儿的名字。她的女儿贝蒂在泰国度假时遇印度洋海啸失踪,爱莎只身到普吉岛寻找女儿。
失去一张好照片,他不会后悔,因为刘宇一贯主张摄影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尊重被摄者。
时间回到2005年1月初,其时刘宇赴泰国普吉岛采访印度洋海啸。一天晚上,刘宇路过酒店大堂时,突然听到有人用中文交谈,回头一看,讲中文的竟是一位黑人妇女。两人就一起聊了起来。爱莎告诉刘宇自己已经年过50了,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世界经济专业的博士学位,说起来还是刘宇的校友。
而最让刘宇吃惊的是,爱莎说她是喀麦隆前国王的女儿,而那时的国王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刘宇了解到,喀麦隆至今还保留着巴蒙部族建立的酋长国,爱莎应该算是这个酋长国的公主了。爱莎已怀有4个月身孕的女儿贝蒂在泰国度假时遇海啸失踪,法国籍男朋友托马斯受伤生还返回了法国。爱莎只身到泰国就是来找女儿的,确切的说是找极有可能已经遇难的贝蒂的遗体。贝蒂是法国籍,法国使馆设在普吉的办公室已经决定第二天带爱莎到重灾区寻找女儿的下落,分手时刘宇只能祝她好运。
再次见到爱莎是第二天晚上在酒店的饭厅里。爱莎面带失望地告诉刘宇,没有找到女儿的线索,但是她根据事先从女儿的男朋友那里了解到的酒店信息,找到了女儿住过的房间,带回了贝蒂用过的一些衣物。法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认为爱莎已经没必要再呆在这里,她准备第二天就回北京。
“我很想去爱莎的房间拍些照片,但爱莎悲伤的情绪使我犹豫了很久是否该打扰她。”刘宇如是说,回到房间,他还是决定先给爱莎打个电话,小心翼翼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并特别说明如果拍照会让她心情更不好,他宁愿放弃。果然,爱莎说见到了女儿的衣物,很难过,还是别拍了。刘宇没有再坚持。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爱莎就打来电话,说:“你要想拍就来拍吧,我想了一夜,决定不走了,继续留下来找女儿。”刘宇到了爱莎的房间,“她用电脑给我放了贝蒂的照片。我也鼓励爱莎留下来,不管结果怎样,至少要尽最大的努力。”爱莎把她的想法跟法国外交官说了,开始法国人担心她一个人在这里会被人骗。爱莎说,这里有她的中国朋友,他们一定会帮助自己的。
当时,刘宇到泰国参加海啸报道半个多月了,返回曼谷的机票就订在当天上午。他让爱莎一起上了新华社的包车,先送自己到机场,然后她继续找女儿。“其实,一路上我的内心都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就这样回去,还是继续陪爱莎找女儿?”刘宇说,“现在轮到爱莎劝我留下来了,望着她期待的眼神,我无法拒绝她的信任——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她的校友。”到了机场,刘宇没有登机,而是改签了机票,一起和爱莎踏上寻亲之路。
他们去的第一站是100多公里外的攀牙府,这里是泰国受灾最重的地区。未经确认的遗体都存放在当地的寺庙里,其中最大的长区寺当时还存有1400具,泰国政府和国际救援组织在这里设立了遗体鉴定中心。爱莎仔细辨认遇难者照片墙上的照片,并向接待人员描述了女儿的身体特征,以及诸如耳环、戒指、假牙、脐环等细节,并提供了贝蒂的照片。工作人员认为她提供的资料非常有价值,但是也向爱莎特别强调所有遗体都已经高度腐败,鉴定比对工作极为困难。
从长区寺出来,爱莎还想再去女儿曾住过的酒店看看。法国人开的索菲特酒店坐落在一片椰林掩映的海边,看起来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穿过废墟他们找到贝蒂和她的男朋友住过的房间,里面一片狼籍。贝蒂刚刚去过北京,所以爱莎几乎认识她的每一件东西。爱莎点燃了路上就买好的蜡烛,嘴里念着贝蒂的昵称:“咕咕、咕咕,妈妈来看你了。”然后,枕着女儿的衣服,躺倒在贝蒂睡过的床上,长睡不起。
出了酒店就是平静的海滩。面对吞噬女儿生命的大海,一直非常坚强的爱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一面按照喀麦隆的传统向着大海撒盐,一边大声呼号:“大海,不要发怒了,还回我的女儿吧!”。回停车场的路上,刘宇走在最前面,担心爱莎看到自己的满面泪水。路遇一个遇难者的祈祷法会,爱莎加入了祈祷的人群。
第二天,刘宇再次陪同爱莎驱车数百公里找女儿。刘宇坦言,当初自己留下来还有为了完成一组报道的因素,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把贝蒂当作自己的亲人,找到她是自己和爱莎同样的心愿。当然,刘宇从没忘记自己是一名记者,但这时报道似乎对他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后来,刘宇接到了总社的调令。在他不得不回北京之前也没能看到爱莎找到女儿的遗体。回到北京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刘宇突然接到了爱莎的电话。她说她最后找到了贝蒂,虽然她失去了女儿,但是中国记者对她的帮助,让她的心里感到了一些温暖。
其实,每一起新闻事件都是有血有肉的。诚如刘宇所言“我们触摸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还有一颗颗滚烫的心灵、一个个感动的瞬间和故事。”
用刘宇的话来说,这也许就是新闻的温度。对于摄影记者来说,照相机不是冷冰冰的金属,而是有温度的,因为它们带着人的体温。要想做出有温度的新闻,除了勇气、坚持、敏锐、勤奋等等,还需要记者有人的良知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01>1999年4月18日,多国部队的士兵抵达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里纳斯机场。科索沃危机爆发以来,大批部队和重武器部署在与南联盟和科索沃接壤的阿尔巴尼亚。
02>1999年4月27日,在阿尔巴尼亚北部与科索沃接壤的库克斯,一架运输机降落在难民营附近的山坡上,孩子们等待分发救援物资。
03>1999年4月27日,在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莫里纳口岸,躲避战火的科索沃难民车队进入阿尔巴尼亚。高峰时这里每天曾涌入四、五万名难民。
04>1999年6月30日,南联盟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的居民乘坐轮渡过江。流经诺维萨德的多瑙河上的三座大桥均在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中被炸毁。
没有一种经历是白费的
《台海》:您是怎样和摄影结缘的?在进入新华社之前接触过摄影吗?
刘宇:接触摄影应该是从高中开始的。我自己动手做过印相机,也买过简陋的放大机,曾经躲在厕所里彻夜不眠。在昏暗的红光下,看到影像从显影液里一点点显现出来,是那个年代难忘的快乐时光。
而且因为我父亲是学美术的,我家的床铺下面有两个木头箱子,里面装着爸爸收藏的一些苏联画家的画册和“文革”前出版的《美术》《装饰》等杂志。我对它们着了迷,翻了一遍又一遍。从中我知道了列宾、苏里柯夫、徐悲鸿、古元、董希文……从那时起,自己也开始学着描描画画。因为每个班级都有宣传栏,我的爱好派上了大用场,经常熬夜画报头到深夜。也因为这样,我的宣传委员一直从小学当到大学毕业。
绘画曾是我上大学时的第一选择,第二选择是建筑设计,都是源于小时候对美术的喜爱。选择摄影也是因为在学了新闻专业后,觉得摄影在所有与新闻相关的行当里离美术最近。所以,美术既是我后来走上摄影之路的诱因,也奠定了早期影像的审美取向。
很多曾经很在意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儿时的某个不经意的爱好,也许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影响,甚至决定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新华社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先后在中央组、新闻中心、采访中心、伦敦分社、华盛顿分社、社会新闻采访室、国际照片编辑室等部门工作,中间还穿插着在中国新闻学院进修、在山西吕梁支教、在山西宝鸡挂职,直到今天有机会为更多摄影人服务。不管愿意或者不愿意,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但是回过头看,没有一种经历是白费的。
比如我现在参与一些展览的策划,很大程度上用到我以前两方面的经历。一方面,我当过10多年的图片编辑,这对选择图片是很有帮助的,因为看了大量的图片;另一方面,展览很重要的就是后期的呈现,我并没有学过设计或策划,但在跟设计师合作时,你会有直观的判断,原来的积累会给予自己灵感和启发。
《台海》:作为摄影记者,您的拍摄经历让人惊叹,先后经历了波黑战争、科索沃危机、伊拉克危机、莫斯科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庆典、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认定、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美英两国大选、四届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报道,说您身经百战都不为过,这些经历对您摄影创作又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宇:这是新华社平台带给我的经历,我在任何时候谈起新华社,我都会觉得是它让我,一个本来对摄影完全不了解的人,慢慢带我走上摄影之路。
有足够的优势,让我参与到很多重大赛事跟决定性时刻。当经历多了、见的世面多了后,更能从个人的角度来认识世界。同时,会从世界的维度来反观自己,而非只是站在井底看自己。
我觉得可以跳脱出摄影。拿这次的武汉之行来说,我觉得它是一次生命的体验或是精神的洗礼。其实,我觉得,摄影最后考验的是你的经历、对生活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这些经历,能够让我从一个更大的格局看待自己、看待摄影。
《台海》:像您每次参与一些大的拍摄行动,事先一般都会做哪些准备工作?
刘宇:我觉得摄影记者就跟士兵一样,在接到采访任务之后,没有什么选择,你背着背包,不管是否准备充分都得上。当然,有的采访拍摄能准备,有的则只能随机应变。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分管体操。我为了了解每个中国运动员的动作特点,我曾经用录像机把运动员的成套动作录下来,再慢动作回放,仔细分析一套动作中,哪个点最出照片,从哪个角度拍最好。比如,我记得女子体操平衡木比赛有个动作叫“鹿跳”,我在国内比赛拍过这个动作,当运动员跳起后,头会后仰。我面对着运动员拍的照片,头会被身体挡住。后来通过分析录像,我发现这个动作在运动员的侧后方拍是最佳角度。在了解运动员什么时候,冲哪个方向做这个动作的前提下,我到了赛场就心里有数了。
我觉得每个采访是不一样的,比如国际上重大事件,就需要对它当下的形势和背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比如1992年到波黑采访,就得对当地民族宗教间矛盾建立基本认知,我觉得作为记者,要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对整个形势有基本的判断,而不至于就是感情用事。

1992年9月11日,在塞尔维亚和波黑的边境附近,一对塞族新婚夫妇结婚第三天就来到波黑战场。
生活本身其实就是最好的摄影题材
《台海》:说实话,我特别好奇您作为战地记者的那段经历。战争充满不确定性,拍摄之前您一般会考虑什么?
刘宇:我们当记者的,一方面要传达信息,告诉读者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基本上起到一个告知的作用。当我们回看以前拍的照片,会发现能留下来的,更多的还是那种充满情感力量的照片。作为记者,照片是传达信息的一种方式,但我觉得在传达信息的基础上,我还希望能够通过照片传达给人的是温暖的或者其他情感的,能够带给别人思考也好,或者能够打动人心也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们当记者之外,其实要考虑的问题。
《台海》:在题材的选择上,有自己的取向?
刘宇:每个摄影人他有自己的题材的选择,但是对于新闻记者来说,特别是在早期,拍摄什么题材,没得选。我一开始到新华社在中央新闻组,前后大家拍中央新闻也拍了十来年,后来也拍体育、文化、社会新闻、国际题材,什么都拍过。那时候也会羡慕别人,有很多摄影师能够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有自己擅长的一个领域。但是对于我来说,倒也不后悔这事,毕竟增加了很多职业经历、履历,就像“万金油”似的什么都拍。
每个摄影人,最大的优势还是他自己的生活。平时遇到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会没话找话地问问对方最近在拍些什么。得到的回答常常是:哎呀,现在太忙了,都没时间拍照片。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拍摄题材和方式,不过在我看来,不是带着长枪短炮才能摄影,更不是安排好的生活才是生活。
有些人喜欢羡慕别人,总是过着一种生活,却又幻想着另一种生活,然后错过了现在的生活。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终究成不了那个我们羡慕的人,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无论是以前还是未来,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和你一样的。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最大的优势恰恰是自己的生活。羡慕别人,不如审视自我。认清自己的短长,做自己喜欢做而且能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当我们认清了自己,或许就成了新的自己。
就我自己来说,以前在媒体当记者,拍过一些大场面和大人物,当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时,作为摄影记者能够恰好在那个时间和空间相交的点上,无疑是幸运的。而现在那些离我已经很远了,但并不影响我继续享受摄影带来的快乐。我现在的工作虽然与摄影相关,但没有多少整块的时间专门用来摄影。要么在家里,要么在工作,要么在去工作的路上。眼下能做的就是尽量把三点一线利用起来:在家,拍家人;路上,拍路人;工作中,拍摄影人。都是不需要东奔西走就可以进行的项目。
生活本身其实就是最好的摄影题材。因为不管多伟大的人,还是多卑微的人都有记录的价值,我给自己做过一个记录短片、也拍过我们家狗的故事,拍上班路上地铁中影像,如果你没有拍照的意愿,会觉得每天坐地铁都是看手机的人,没什么差别。当你放下手机,观察周边,就会发现地铁车厢就是一个小社会,你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画面。在我的工作中,接触最多的是摄影人,我也会记录他们放下相机后,生活中的模样。

1999年7月29日,一名妇女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郊区的墓地扫墓。波黑战争中有27.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

01>2003年2月10日,在与伊拉克北部接壤的土耳其小镇锡洛皮,特种兵在街头警戒。
02>2003年2月28日,在伊拉克北部城市埃尔比勒的老城,孩子们在踢足球。
03>2003年3月7日,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外,一位名叫希纳的男孩吊在足球大门上。
打动人的讲述需要细节
《台海》:我看您分享的《武汉手记》,您拍摄的作品都会像这样记录图片背后的故事?
刘宇:这是第一次。面对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身处世界瞩目的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武汉,职业的使命感支撑着我一定要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在武汉期间,我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发表了26篇、6万多字的手记。我在每一篇手记后,都写了一句话:如果不记下来,我怕将来会忘记。这给我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基本上白天拍照片,上半夜整文件,下半夜写文章。经常在熬了整夜,拭干眼泪之后,可以听到窗外的鸟鸣。我把武汉之行当作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倍加珍惜。
我是武汉的女婿,在拍摄医务人员肖像的同时,我尽可能挤出时间记录封城下的武汉人的生活。一开始我没有给自己设定主题,当我回过头来看,其实是说的一件事,就是大疫之下的大爱。那些普通人身上闪烁出人性的光辉,无时无刻不带给我感动。如果不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下,我很可能会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让我明白,走进另一个人的内心并没有那么难,只需要从一句真诚的问好开始。人和人之间只有一颗心的距离。武汉之行也让我再次深刻体会到,文艺创作也好,新闻报道也好,深入生活都是不二法门,你比深入再深一尺,那些鲜活的人和事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有不少人和我说,去了武汉多出大片。说心里话,我们不是为了追求那一两张大片去武汉的,我只是希望把用心感受到的东西,通过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篇文字、甚至是一首歌传播给受众,可能我们捡拾的只是一些碎片,但当把这些碎片拼合起来,碎片越多,拼合而成的画面就会越完整,让现在和将来的人们,了解武汉发生了什么。
《台海》:有人说过:您的照片“有一份特别的宁静和悲悯”,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刘宇:我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照片就是什么样的。摄影者的性情与好恶一定在照片里。我总觉得好的新闻照片,也不一定是激情爆发的那一刻,即使在激烈冲突的地区,拍摄时,他不会忽视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关照。也可以是一些安静的画面来呈现温暖的瞬间。
1992年10月,我奉新华社之命采访波黑内战。从贝尔格莱德前往波黑塞族武装的中心帕莱,刚进入波黑境内,前方的车队就被穆斯林武装袭击,我们被迫滞留在边境附近。一名当地的记者得知我来自中国的新华社,主动带我到附近的医院,看到了被杀死的十几个平民的尸体全部被烧焦了,有些头甚至被割下。我拍了照片,但没有发稿。我觉得,揭露战争的罪恶不一定非要用赤裸裸刺激读者神经的方式。
等回到滞留的地方,我看到来时同乘一辆车的一对身穿军装的青年男女依偎在山坡上,女的怀里抱着一只流浪的小猫,一脸甜蜜。男的目光悠远地望着前方。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来自远方的中国记者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在路上他们的战友曾告诉我们这对夫妇刚结婚三天,他们的愿望是生六个孩子。爱情孕育生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命不被战争吞噬呢?摄影记者当然要反映战争带来的后果,但同样不能忽视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关照。后来我记得有一位老师对该作品如是评价,“新闻记者能够跳出新闻事件,能够更注重情感,我觉得是中国新闻摄影的一个进步。”

2015年,波兰卢布林。一位老人在火车开动后,望着渐渐远去的送行亲人。
《台海》:摄影创作过程中,让您最享受的是什么?
刘宇:我很感谢摄影,记得1999年科索沃危机时,当时我在阿尔巴尼亚,其间,辗转到马其顿、南联盟,我们就围绕着巴尔干这个地方转。有一天,我和同事开车到奥赫里湖,那是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交界的地方,景色特美。当时我坐在那里,如果不是因为摄影,不是因为当了摄影记者,怎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摄影记者,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故事,每天生活都是新鲜的,可以在世界的每一个拐角看大不同的阳光,珍藏不同路上遇到的每一张笑脸,还可置身在那些重大事件、时间、空间的交汇点上记录这个世界不同的侧面。你可以把别人的日子中某一个瞬间定格,通过这个照片讲述这些人的故事,我觉得这可能是摄影让你最享受的地方,也是摄影最美妙的地方。
《台海》:您觉得什么是好照片?
刘宇:什么才是好照片,一个日本摄影师说过,好照片就是翻开老照片时带来的感动。拿这次武汉之行来说,为4.2万名医务人员拍摄肖像,无疑是世界摄影史上的创举。在几十位摄影师的努力下,完成了当初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在拍照片,而是以摄影的名义,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敬意。也许那一张肖像和别人没有关系,也可能定格的不是他们最好看的样子。但我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留下的瞬间,对于他们,对于他们的家庭,可能就是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当我脱离新闻摄影圈,接触了更多类型的影像,见到了数不清的符合规则、技巧完美,但就是不打动人的照片。好看、漂亮不是判定照片好坏的一个标准。我常常觉得,照片过于“完美”反倒显得匠气。摄影当然有自己的语言,就像写文章需要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一样,但掌握了技巧,不一定就能当作家。我觉得,不能用一种标准或普遍的意义去定义或衡量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照片,其实好照片可以是任何样子,或者说摄影可以是任何样子。

刘宇:拍照这件事,技术比器材重要;想法比技术重要。我参加过很多关于摄影的评选、比赛、展览等工作,留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很多照片看起来似曾相识,无论拍摄的题材还是表现的方法,好像是同一个人拍的。
但摄影对于不同的人,它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职业记者而言,他的使命是时代之眼,要记录现实、留给历史;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摄影师来说,摄影可以是任何样子。但如果你希望在摄影上走得更远,一味地模仿,肯定行不通。
其实说摄影难,所谓难就难在太容易了,摄影的门槛是非常低,只要有一部手机,谁都是摄影师。但其中哪怕有一张能被许多人记住的照片,有吗?太少人能做到了,这也是摄影最难的地方。
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呈现的方法上,能够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标签,这是非常难的。如果要我说有什么忠告,我觉得还是拍自己,看见自己。
《台海》:您可能策划或参加、举办过很多重大的摄影赛事或摄影活动,我们台赛今年也就即将步入第十年了,对于如何进一步扩大赛事的影响力,您又有何建议?
刘宇:我参加过第一届台海新闻摄影大赛,其实,这之后,我也投稿过,可以说跟台赛挺有缘的。台赛能走到今天也挺难得的。因为这个活动,我也认识了不少台湾摄影师,平日里联系也挺多的。但近几年,可能跟大背景有关,两岸的摄影交流相对少了。
其实,我觉得摄影最好的交流,是人员间的交流。大陆跟台湾都有很多非常棒的摄影师,如果大家的作品能够彼此交流,在两岸轮流展览,通过图片的方式,让台湾人更多地了解大陆现在的生活,让大陆人更多地了解台湾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摄影能够做到的最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