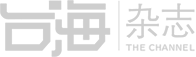讲述/张维维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 张铮 图/唐光峰 受访者提供
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简称《告台湾同胞书》)正式发表,郑重宣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台湾回归祖国、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1800字的《告台湾同胞书》语重心长、情理交融,改变了许多台胞的命运,他们受到感召,热烈响应祖国的呼唤,跨越重重阻碍回到大陆,台胞张维维一家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那个时代,成功回到祖国大陆的台胞并不多见,能够举家迁往大陆的几乎不可能,这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张维维笑容轻松地说着他的经历,平静得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11岁跟随父母来到厦门,张维维的成长过程也是见证大陆飞速发展的过程。曾经天真无邪的少年如今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多少次梦回儿时与玩伴最爱去的台北“新公园”,当理想与乡愁不可避免地被放在天平的两端,他依然坚定地站在这里。他说,这是一种信念。

张维维
曾任厦门市政协委员
1970年出生于台湾台北
1981年,11岁随父母举家来到厦门
2011年,第一次与台湾亲友见面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揭开了两岸关系新的一页。1981年,11岁跟随父母来到厦门,张维维的成长过程也是见证大陆飞速发展的过程。
懵懂中来到大陆
1970年,我出生在台北。母亲是台南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我们一家是响应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回归祖国大陆的一代台胞。1981年,我们一家人从台湾迁往厦门生活,那一年我11岁,读小学六年级。
那时的我没有什么两岸的概念,但在懵懵懂懂中,从父母对话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了离别的气息。我对童年的玩伴说:“我可能要离开台湾,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一年,那一天。父母带着我在最喜欢的台北“新公园”玩了很久,平时他们都会在落日时分匆匆叫我回家,可是那天直到夜幕降临,月亮爬上树梢,公园里只剩寥寥无几的人时,他们还没有叫我回家。我感觉很奇怪,却也没有说破。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新公园了,也许是父母希望我在这里玩得尽兴,以供日后慢慢回忆吧。
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未来会跟随父母去哪里。那时候举家离开台湾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更何况去大陆。父母对我们要迁往大陆的消息做了充分保密,所以连我也不知道。我们对外一致宣称,我们是去日本旅游。直到我们辗转日本,父母才告诉我,我们这是要去大陆。年少无知的我对新生活充满了好奇,同时也带了些担忧——毕竟我在台湾时总是听别人说,大陆的小朋友过着“连香蕉皮都吃”的生活。
当时年纪小,我只记得父母通过很多渠道的帮忙,我们才在三个月后终于拿到了从日本东京到大陆的通行证。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时,我惊呆了——这样的场景,我以前只在描写过去年代的电影里才能见到。更夸张的是,我居然看到了在我认知里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的蒸汽火车还在铁路上行驶。这一切来得太梦幻了,我感觉自己穿越了时空。
我们被安排在宾馆暂住,每天的餐标四菜一汤,其实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的标准及待遇了。但对于在台湾时家境优渥的我来说,其实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我想不通,父母为什么愿意放弃在台湾那么好的生活条件来到大陆。
长大后,我慢慢理解了父亲来到大陆的原因。在我的父亲那一辈,从小看得最多的就是战火纷飞、生离死别,父亲总是在说:“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带着这个问题,他成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第一届的毕业生,企图在学习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他的老师意味深长地告诉他:“没有这么容易。”而他来到大陆,或许就是希望一个答案吧。后来,他到厦门大学任教,继续走在寻找这个答案的路上。

二十多年前,张维维(左)与弟弟在厦门大学内的合影。

20世纪80年代的厦门双十中学校门,张维维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中学时光。
三十年后重回故乡
我在厦门双十中学,完成了我初中、高中的学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双十中学在特区的教育队列中独领风骚,是福建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之一。迎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越来越多台胞辗转来厦寻根谒祖,以民间交流的“小门”打开了两岸交流交往的“大门”。同时随着在厦台企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台胞台商扎根厦门,因此我的同学中也不乏和我一样的台籍身份。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留在了厦门工作。2011年,我因公出差前往了台湾,这是我时隔30年第一次回到台湾。其实,这也是我母亲与台南的外公外婆断绝关系的第三十年。父母与外公外婆都是执拗的人,在此三十年间,我们彼此间无一封家书。
尽管有埋怨,但时隔多年,外公外婆再见我时我已人到中年,说不想念我是假的。大表弟热情地迎接了我,小表弟不待见地撇了撇嘴,但无论如何,我都为这场来之不易的会面感到由衷的开心。外公外婆软硬兼施,希望我不要再回大陆,屡次想让姨妈直接给我办上台湾的身份证,但我都婉拒了。我知道,我的根在祖国大陆。
当我重新踏上返回大陆的旅程,一如三十年前父亲离开时那样,耳边响起了父亲时常教导我的话:“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不是喊口号的一句话,而是父亲发自内心的信念。不只父亲,在我看来,母亲对信念的执着,完全不亚于父亲。她出生在深绿的家庭,宁愿和家里断绝关系,也要坚守自己的信仰。早在90年代初期,我母亲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五届福建省政协委员,在任时间长达25年。
直到今天,台南的外公外婆二老与我们依旧没有直接联系,他们有自己坚持的东西。外公外婆时常让我多回台湾家中看看,老人家年事已高,虽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但总归是一份殷切的期盼。多年来,我早已在厦门安家立业,唯一的女儿也留在了厦门工作,这样的生活挺好。

2020年,张维维在“祖国大陆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平潭留影。
从一小步到一大步
在祖国大陆,我去过两个地方,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广州的黄花岗与南京的雨花台。它们一个是老一辈资产阶级革命的纪念圣地,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纪念圣地。这些伟大的革命烈士,都是有信念的人。他们明知将会面对怎样的结局,却心怀大义,慷慨赴死。他们用鲜血和信仰铺就了一条救中国的路,让我心生敬仰。
长在红旗下的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这么多年来祖国发展的迅速,以及这一路走来的艰辛。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不要以为你碗里多一块肉有多么普通,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就需要多十几亿块肉。”每个人的生活多一点点的进步,都是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步,老旧的蒸汽火车也真的进入了博物馆让位给了驰骋于神州大地的高铁。小步也好,大步也罢,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来的,实属不易。
如今我跟别人介绍自己是哪里人的时候,我通常会说“我是厦门人”。一方面,台籍身份多多少少让对方觉得有一些特殊性,另一方面,四十年的厦门生活,我早已习惯这个温暖的家。
我曾经是美资高科技企业在大中华区物流/供应链负责人,因此时常与台湾的供应商联系。在日常工作沟通中,他们常常觉得我有些“不一样”,直到后来我透露自己出生在台北,曾在台北生活了11年,他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好像总觉得什么地方跟他们与我其他同事沟通时不一样的感觉。这件事也从侧面证明,两岸的交流方式、思维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尽管两岸同根同源同种,但长久以来的分隔,让彼此之间有了许多无法相互理解的地方,因此也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隔阂。
最令我难以置信的事,就在几年前居然还会有“台湾人民认为大陆人吃不起榨菜”的事情发生,这不免让我想起了四十年前那个以为“大陆小朋友吃香蕉皮”的自己。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被遮蔽的双眼依旧没有被打开,这样可笑的新闻经过深思,是可怕的。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何时才能将心态和认知的差异消除?在我看来,通过沟通交流,消除彼此间的误会,找寻文化认同,倾听民心所向,是消除隔阂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