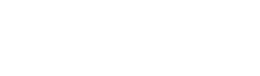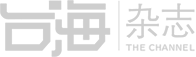人的经历很奇特,绝大部分终究会随风飘走,而一旦留存在心间的,哪怕过了十年二十年,只要有只手轻叩心门,埋藏心间的那些人和事便会被唤醒,他们情不自禁地打开心门,走出来,活灵活现地站在你的眼前。
那天,我参加了《福建海防前线三十年(1949—1979)》新书发布会,原本风平浪静的内心,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心潮澎湃。民兵队长林水仙、风筝姑娘郭秀玉、海上救护员蔡南平、船老大余福……他们踏波而来。20年了,在我的心中,他们容颜未改、声音依旧。
20年前,2004年春天,我刚刚实现从小的梦想——成为一名记者,便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64岁林水仙,她个子瘦小,走在人海中可能一下子被淹没。我抓住她不放,紧随其后来到了浯屿岛。
浯屿岛在哪里?浯屿岛四面环海,隶属龙海市港尾镇浯屿村,与厦门相距约为8公里,与金门二嶝岛相距约为4.5公里。如果不是地处福建沿海前线,如果没有海峡间的磕磕碰碰,如果没有那支女民兵,浯屿岛与其他渔村没有什么两样。但偏偏这些都发生了,这就注定了浯屿岛成为人们文化地图上的一个精神符号。
林水仙何许人?林水仙于1940年出生于浯屿岛,16岁成为浯屿民兵营营长,18岁率领民兵营参加了1958年金门炮战,同年,赴京出席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表彰会,获福建省劳动模范殊荣,是电影《海霞》的原型之一。
我和她坐在从岛美到浯屿的一叶扁舟上,海浪一次次把我们推高又放下。她的故事也随着波浪起伏不断。除了抓水鬼,向对岸空飘、海漂宣传品也是女民兵们的日常工作,金门炮战前夕,有两回,水仙她们竟然在枪林弹雨中把“统一祖国”的标语插上了敌占岛。1958年7月,海峡两岸战云密布,浯屿岛居民将全部撤到后方。24位民兵却留了下来,他们中间有4位女民兵,她们是林水仙、郭秀玉、林碧云和林玉花,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林水仙望着海面,回忆起当年撤离的情景:“做父母的没有一个舍得孩子留在前线,因为谁都明白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但没有哪对父母阻止孩子留下来,因为他们比谁都明白祖国需要这些儿女们!”
上岸后,我遇到了来迎接林水仙的郭秀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所以我们亲如兄弟姐妹;可能因为有颗忠心,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死亡!”郭秀玉参加女民兵时只有十五六岁,我采访她时,她是一位在浯屿岛上织着渔网的六旬老太。
她俩又带着我采访了蔡南平和余福。
1958年炮战期间,厦门到浯屿岛建起了海上交通线,从厦门运输粮食、木柴和信件到浯屿岛,如果岛上有官兵受伤,就从这条交通线把伤病员从浯屿岛护送到厦门抢救。在这条交通线上,敌人的炮火最为密集,因为切断交通线,就意味着切断我军的生命线。而蔡南平就是在炮火纷飞中来回于这条交通线上的民兵。采访他时,蔡南平的家是一座闽南红砖厝,院子里种满花草,他就在花香里对我回忆起四十年前的往事,面容平静。
船老大余福接受我采访时已78岁了,住在浯屿岛上一间老旧的平房里,他的住处与周围拔地而起的高楼很不相称,可余福却平静地告诉我,他和老伴住在这里僻静安闲,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在保卫福建沿海前线的战斗中,他带领船队发展生产支持前线,所以1957年被评上省劳模。
采访中,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理由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出了自己。
2004年的那次采访,我在厦门日报上写了含五个大版面的专题“呼唤忠诚”,并在卷首语上写下了思考的答案:“只有一个理由让他们无所畏惧地面对孤独与死亡,这个理由,就是——忠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这对初为记者的我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教育。
20年后的今天,当心中那片海再次传来涛声时,我知道那是林水仙他们的足音,我侧耳倾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什么时候钩沉,都不过时,都会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