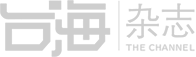文/《台海》杂志主编 年月
在离开双第华侨农场时,50多岁的张松勇说:“你们是几十年来第一批夜宿双第的外来者。”张松勇是土生土长的双第人。他口中的“你们”,除了我,还有台湾中国时报摄影中心主任黄子明和台湾世新大学副教授陈学圣,两位都是在两岸有影响力的摄影家。
那时双第没有旅舍,为了能够夜宿农场,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联系上素未谋面的双第人张松勇,电话线那头传来他热情的声音:“住在我家吧,只是担心你们嫌弃。”哪会嫌弃呢?能与双第乡亲同吃同住,我们巴不得呢!
出发去双第的白天,我接到了张松勇的电话,他说,父母在打扫房间时,发现凑不到四间房给我们住,张松勇的哥哥、双第小学校长张松木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解燃眉之急,“住到小学里。” 双第小学并不是寄宿制学校,也就没有被席,兄弟俩当天跑到县城,帮我们买回了四套被席和洗漱用品。
所以,在还没有到双第采风时,我们就已经被双第人的热忱所感动。张松勇与我素昧平生,可一听说我们要去他的家乡采风创作,他就如此热情地为我们解决难题。作为第一位我接触的双第人,未曾见面时,他就留给了我们淳朴、热情、豪放,甚至是侠肝义胆的形象。因此,尚未踏入双第,我们就对双第心生好感。
这个美好的序曲是诞生于新冠疫情发生前的某一天。当车子进入双第地界时,夜色已深。路上空无一人,但一路上,我们并不孤单,总感觉不远处,万家灯火正在迎接我们。
“双第”之名,缘起于漳州第一位进士周匡物与兄长周匡业,两位兄弟参加科举考试前均在此苦读,弟兄俩先后考中进士后,唐天子即赐名此地为“双第”。
唐朝的双第是一幅什么模样呢?感谢周匡物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诗句:“窗外卷草侵碧苔,槛前敲竹响青冥。黄昏不欲留人宿,云起风生龙虎醒。”有人说,这首诗反映了一千多年前的双第人烟稀少、虎狼啸聚的荒凉景象。可在我读来,眼前展现的却是碧草连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景,我尤其喜欢“窗外卷草侵碧苔,槛前敲竹响青冥。”读着读着,闭上眼睛,仿佛天籁传来。
即使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文明进程,双第依然不改青葱模样。夜宿双第小学那晚,我们看到了在城里多少年看不到的满天星斗,听到了如一夜笙歌的蛙鸣,闻到了夹杂着泥土与牛粪的青草味。黄子明老师干脆赤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说,脚底没有一丝灰尘。走了几圈后,连脚都不用洗,我们便沉入了甜美的梦乡。
醒来后,已见天亮。也就在这一刻,我们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双第清秀的面容。黄子明老师问当地人,双第海拔多高呢?也许在他想来,只有高出平地许多,才能留有这般容颜,当地人答:“我们比平地还低,是盆地。”
当然,双第之所以吸引我们前往,并不只是一千多年前的周氏兄弟,更因为它曾于1960年到1979年,13次接收了从印尼、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归来的4719名华侨难民,并因此成立了国营华侨双第农场。成立之初,农场有160户830位本地人与4719位华侨合并,农场人口最多时上万人,不只有场部,还有学校、医院、派出所等机构,而养活他们的是从荒野中开恳种植出来的希望的田野,高处是茶山,低处是稻田,而中间则是果园。茶厂、糖厂、米厂、砖瓦厂、榨油厂和综合厂也应运而生。
当然,时过境迁,工厂已关门,重新开张时,已是文创园;果园,也变成了观光园;农场,现在叫经济开发区。而不变的是双第人对泥土的深情。
在双第采风的那几天,我们又结识了数位归侨子女,黄爱云便是其中一位。
1960年,黄爱云两岁。父亲黄坤河带着全家六口人从印尼回来,父亲出任大队长,母亲在糕饼厂上班。“我父亲很爱国,他一直珍藏着周总理到印尼出席万隆会议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他在印尼买的,他总是对我们说‘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才不会被欺负’。”
“总是斗志昂扬!”她说。随着黄爱云等归侨子女的追忆,父辈和许多归侨建设农场的高涨热情扑面而来……
而今,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还有华侨后代制作的素味千层糕。淡淡的、甜甜的乌糖香,正召唤着我们:“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