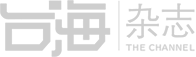癸卯酷暑的一天,接到老洪的电话。
电话里,老洪说,他已近耄耋之年,想写一本回忆录,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一个句号。他问我能否给予“指正”,如果有空,写几个字“鼓励”,他将“感激不尽”。
老洪的一席话,让我羞愧难当,就凭跟老洪整整18个年头的交往,我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婉拒。
于是,老洪断断续续将其回忆录的部分章节发给我,我也利用业余时间先“读”为快。
我将全书一字不落地读完,不禁感慨万千:老洪的人生,是一部丰富多彩又曲折传奇的大书,足够后人一辈子阅读、一辈子学习。
我这么说,绝无丝毫的溢美之词;如果你有幸读到老洪的回忆录,或许也会认同我的看法。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复述书中的内容,仅谈点与老洪交往的点点滴滴。
老洪大我一轮,都属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的兄长。这不仅仅是年龄上的,更重要的是业务方面。我是1997年进入厦门日报社的,三不五时就得值夜班。那时候,编辑部还没有实现“无纸化”办公,写稿、改稿、审稿、签发大样,全靠一只手、一支笔。我长期在报社工作,对文字的要求,几乎到了洁癖程度。也因此,我对写得一手好字、一纸好文章的人,平添几分敬意。所以,已是部门负责人的老洪,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我的视野。
“笔力”对于记者来说是文笔之美、成文之巧;对于编辑而言,则是为人作嫁、成人之美。老洪修改过的稿子,一笔一划,一撇一捺,都经得起推敲。编辑要根据记者的初稿进行二次创作,有时记者为了第一时间发回稿件,写得不够细腻;有时因为记者还要继续跟进采访,写稿时间不足;有时一篇稿子是多个记者同时在采写,就得有人统稿,但无论哪种情形,最后的都得有为人作嫁的编辑。在我眼里,老洪就是那样的编辑。
老洪不仅稿子改得好,文章也写得好。他总能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思想;用最精细的笔触,描绘最生动的画面。他的文章就像他的人一样,简洁而不简单,深沉而不浮夸。仅这些,就让我自叹弗如。
一次,我曾向老洪请教为文之道。他没多说,只是问我,知不知道徐祝庆?我说,当然知道,徐祝庆是中国青年报社长,他的文章常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我也常将其作为范文认真学习。听我这么一说,老洪显然有些得意了:“徐祝庆和我是同班同学。”难怪,他们都是1962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我当然不是“唯成分论”者,但“文革”前科班出身的老洪,绝对没有辜负母校对他的培养。末了,老洪还跟我聊起他当年从集美中学参加高考时写的作文。他说,当年的作文题,一题是《雨后》,要求写一篇记叙文;另一题是《谈不怕鬼》,要求写一篇论说文,二者选其一。他略为思索,选了后者。他的文章大意是:这世界上既没有鬼又有鬼。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相信科学,破除迷信,不信鬼,不信邪;但我们又是共产主义者,要同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鬼”——譬如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种反动势力,以及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自己脑袋中的私心杂念等各种各样的“鬼”,进行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老洪说完,我看得出来,他还是有些得意。不过,老洪是有资格得意的,我也由衷地佩服。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就这样,我跟老洪成了莫逆之交。
彼时,厦门日报社旧址在深田路46号。因为不少员工是“三班倒”,办公楼旁的旧二轻宿舍楼下的报社食堂,一日提供五餐,早餐、上午点心、午餐、晚餐、夜宵。我跟老洪——当然还有其他同事,因夜班,常常一日三餐(午餐、晚餐、夜宵)聚在一块吃大锅饭。
夜宵后,还要等校对、排版、出样、审样、签样,中间可以休息一两个钟头。此时,若是月明星稀,我跟老洪就经常到中山公园散步。我们几乎无所不聊,聊得最多的,还是老洪种种的人生际遇;其中的一些片段,引起了我的共情。老洪与我一样,出生在南安县的山旮旯里。他的故乡与我的故乡,处于戴云山余脉,近一山之隔。旧时的山村,借用宋代释普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终日提纲,神号鬼哭”一诗来形容,怕也不为过。好在上苍对老洪、对我的眷顾,让我们走出大山的怀抱,自此有了别样的人生。但是,人生路上从来都不是一马平川,几时起几时落,浮浮沉沉;几时哭几时笑,悲悲喜喜。这些,在老洪的回忆录里,皆有详尽的记录。
在我看来,老洪写回忆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蓄谋已久”。他以时间为轴,以自己的成长为线,呈现了他一生的故事和独特的轨迹。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他渴望自己的人生轨迹,能给后人有所启迪。
老洪做到了。人的一生福祸无常,风云难测,好运与厄运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个人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最佳状态,做到在顺境中有否定自我的勇气、在逆境中有百折不回的骨气、在绝境中有挑战人生的豪气。大凡细心的读者,都能从老洪的回忆录里读出他的言外之意,我也不再饶舌。
老洪跟我说,他在厦门日报社工作了整整20个年头,我也一样。
人生能有几个20年?20年,说长也长,7300个日日夜夜,每一分每一秒生命都在更迭交替,万事万物都在静寂中发生着变化;说短也很短,短得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咂,回味它的美妙,已被匆匆拖入了老年的行列。20年,经历了多少无奈与艰辛,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实,渐行渐远的红尘往事,司空见惯的世态炎凉。对此,我跟老洪一样,也曾伤心过、痛苦过,微笑过、落寞过;但是,当我回忆起与老洪一块工作过的日日夜夜,总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是那么的舒心,那么的温暖。
记得1999年10月9日,第14号特大台风正面袭击厦门,给厦门造成巨大损失。老洪已经连续三天三夜随访报道市领导下基层检查指导防台风和重建家园工作,他的体力和精力无疑已到极限;但是,当天早上,报社接到一个任务,要采写一篇全方位反映厦门军民抗击14号特大台风的长篇通讯,而且要求三天之内完成。谁来完成这项艰难任务?我首先想到老洪。当我向他传达上级精神时,他二话没说,爽快接受。三天后,15日深夜,老洪将稿子交到总编室。16日早晨,13000多字的长篇通讯《特区儿女抗天歌》,在《厦门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好评。
老洪的勤业、敬业、精业,有目共睹。次年的2000年9月10日,是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经报社上下一致推荐,老洪被评为福建省首届双十佳新闻工作者和厦门市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当时,《厦门日报》资深记者吴瑞生采写了一篇有关老洪的人物通讯。那天,恰好我值夜班,我直接将原文较为冗长的标题改为《记者洪涛》,而且配发了老洪采访刚刚就任厦门市市长朱亚衍的照片;次日,编辑部电话铃声响个不停,纷纷给报社点赞,给老洪点赞。那时候,党报的权威性、影响力,是今天无法想象的。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往事飘飘渺渺,似过眼云烟,回忆中的故事,在我以为的永远里,悄悄改变。2005年,是我担任报社主要负责人的第四个年头。4年来,我与我的同事,守正创新,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前提下,对报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中,老洪等中层干部给予了我信心与力量。但是,一转眼,是年的10月份,办公室同志告诉我,老洪11月份就要退休了,谁来接过他的担子,要我有所考虑。这的确让我一时很不适应。老洪在报社从事党政报道将近20年,责任重大,压力山大,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老洪以他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一贯作风,在采编岗位上从未有过大的差错。我们常说,这个世界离开谁,地球照转;这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具体到个例,人与人还是不一样的。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老洪退休的前一天晚上,我跟几位同事,在报社食堂,自备薄酒,为老洪举办退休欢送会。大家一起回顾了老洪踏足新闻行业30年的风雨历程,真诚感谢他为党的新闻事业、为报社做出的贡献,并送上美好的退休祝福。老洪也深情回顾和总结了自己职业生涯,讲述了自己和厦门日报社的情怀,表达了对报社工作的无限祝福和惜别之情。
老洪退休时,我还不到50岁,似乎离退休还有那么点距离;但我经常对报社的同仁说,老同志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言下之意,就是在职的同志要多关心、理解老同志。没想到,转眼间,我自己也成了老同志。退休后,几次在路上偶遇老洪,他还是背着他过去背过的那个旧挎包,他还是低着头步履匆匆,如果不是我叫他,他压根看不见我。他感叹说,自己已是“廉颇老矣”,而我还年轻,令他非常羡慕。我笑了,对他说,人生的每一步,多一步少一步,最后都是殊途同归,我也很快就要追上他的脚步了。人间沉浮事,摇扇一壶茶,大家一起共勉。
不知哪位哲人说过,我们经历的岁月越多,仿佛值得回忆的人就越少;但那些历经时光洗礼过而依然鲜活的故事,却有着生活磨灭不了的属性。老洪与我,已远离江湖,但他的故事依然鲜活,他是值得我回忆的少数人之一;能借其回忆录付梓之际,写下一点体会,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