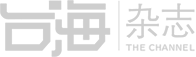如何写一个好的故事?不同的作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对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朵拉来说,所谓好的故事不一定是美满的结局,或是给予读者人生的解答;有时也可以向读者抛出问题,引导他们自己寻找答案。她就是在日常的节奏里,创作出了发人深省的日常。

朵拉(右)接受泉州电视台《咱厝人》栏目采访,讲述她的家庭与闽南的深厚渊源。
习惯的养成向来不易,不过假如是具有仪式感的习惯,想必就不会轻易放弃。对朵拉来说,早晨的时光就因仪式感的习惯而与众不同:她总在相对固定的时间醒来,简单的运动锻炼及享用早餐之后,便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这是她头脑最清醒的时刻,也因为此刻家中无杂事打扰,更容易集中注意力,让流动的灵感经由笔尖倾泻于纸上,正如她所说:“我深爱文学创作,我要我的创作永远没有停滞状态。”
抓住生活中的美
朵拉说,自己的皮包里永远带着一本子,便于随时记录下偶尔迸发的灵感。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事物,有时是一朵花、一棵树,哪怕仅仅是一幕一闪而过的风景,都可能触动她的感官,萌生一个模糊的概念,并由此展开思考。她的微型小说《人行道上的镜子》的诞生,就是源于某一天她在路上见到两个人扛着一块大玻璃镜子穿过人行道的这个瞬间,“我花了三年的时间,在这个简单的画面上寻找故事,后来完成了这篇微型小说。”
这篇小说一开头便悬念感十足:主人公罗丽美混在行色匆匆的人潮中,突然她发现有一位外貌及装扮都与自己相似的女孩正朝自己走来,走近了才发现是一面摆在人行道上的镜子;然而故事并未就此戛然而止,罗丽美发现镜中人并非全然真实地反映出自己,无论自己如何微笑,镜子里的“罗丽美”始终郁郁寡欢。第二天当再次经过那条路,她却发现镜子的角落出现了一个女孩子的雕画,面对这一连串的奇遇,她却无法与人分享——除了她,无人在意那面镜子,也看不见那个雕画。小说最终以一句“走呀,罗丽美。”落笔,给读者一个充满余韵的留白,这究竟是主人公的一场幻想,还是作者的一个暗示:倘若一味地朝前赶路,势必会错过生活中那些细微的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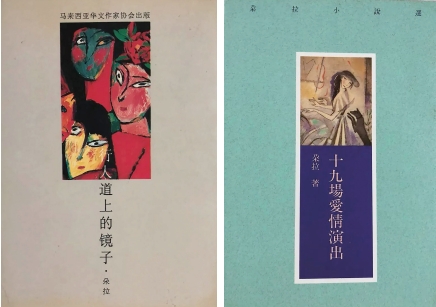
朵拉小说集《行人道上的镜子》和《十九场爱情演出》,她擅长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生动的人物形象,并带给读者意味深长的思考。
《人行道上的镜子》全文仅一千六百多字,这篇短小精炼的小说还获得1993年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并深得评论家好评。2013年,莫言担任2013年“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的终评委主任,他为朵拉那篇获奖作品《那日有雾》写下这样的评语,“富有诗意,充满象征意味,突破了微型小说写作中司空见惯的模式。”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袁勇麟也曾评价朵拉的微型小说,是“突破了突变手法的叙事局限性,引入散文抒情式笔法,将突变的紧张情节冲突和缓慢的悠远情绪铺垫相结合,达到回味无穷、引人深思的效果。” 诚如他所言,朵拉所创作的微型小说,准确地抓住了这一文体的精髓,即通过精炼的情节、凝练的语言及精心的经营,生动刻画人物形象及个性,把控故事的节奏感,引申出意味深长的主题及思想。“另外,还要重视留白的艺术,通过各种隐喻、象征或反讽手法让读者在短暂的阅读中获得审美的饱满。”朵拉如是说。
以文学为女性发声
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引发了朵拉诸多思考,尤其当她回到马来西亚之后,通过有意识地去观察和体会,她更意识到马来西亚同样也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当时,马来西亚有很多作家都为颇为敏感的种族和教育这两大话题写作,阐述自己的观点;然而面对长时间遭受性别歧视、承担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以及家庭责任的女性,却鲜有人为其发声。因此朵拉下定决心:“要通过文学创作来为女人说话,把她们在社会、家庭和个人所面临的压力、挑战和困境,包括人生经历,情感体验和内心世界,让更多人看见和了解,也希望通过作品展现她们在面对种种不公平现象时的坚韧的精神和奋斗的勇气。”

1993年,朵拉到厦门大学进修,由此对女权主义及妇女文学有了更深的了解,图为朵拉(右三)与当时的厦大教授们合影。
1993年,朵拉前往厦门大学进修,她特别选择了“女权主义与中国妇女文学”这一课题,进修的那段时间,通过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朱水涌的指导,她广泛阅读不同文体的女性文学作品,接触了不少西方作品翻译的包括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和观念。这段经历对朵拉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令她对女权主义及妇女文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激励她以女性视角去反映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体验,倾注对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热情和动力。还因为朵拉所生活的马来西亚槟城,属于闽南人聚居较多的城市,她在创作时自然将马来西亚及闽南地区的女性作为重要角色进行刻画。《单身女郎》这部作品中,朵拉刻画了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拥有一套自己的价值取向及生活观的独立女性;哪怕是在描写婚后家庭主妇生活的《惆怅旧欢》里,朵拉笔下的主人公在面临婚姻危机之时,也没有一味地忍让,而是通过“从衣橱最上方找出自己的文凭,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征聘启事”这一举动展现“她”的觉醒,其中“用熨斗仔细烫过(文凭)”这一细节,更是向读者传递出主人公坚定的决心,足见作者的笔力以及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家庭的文学启蒙
“有时候朋友会笑着问我,为什么你不管任何东西,都要和写作扯上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出于情不自禁吧!”朵拉直言自己太喜欢文学创作,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都可能激发她的创作灵感,这种强烈的敏感度正是作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同时她也强调,灵感并不是突然凭空出现,是需要生活的累积,思想的深度。
对朵拉而言,文学方面的积累从她小时候就开始了。在她记忆中,从小生活的那条街上,只有她的家庭有订阅报纸杂志,每天一到下午,左右邻居都会来家里借阅,“那时候我接触到的书刊以香港出版的居多,我叔叔会定《武侠世界》,姑姑定《南国电影》,我还读过《儿童乐园》月刊,基本都是华文读物。” 在阅读氛围浓厚的家庭长大,培养了朵拉爱阅读的习惯,后来她在学校的图书馆又接触了许多文学书籍,譬如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有《钟楼怪人》《基督山恩仇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当时她并没有要成为作家的意识,仅仅是被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而不愿放下手中的书,然而这些扎实的阅读积累,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了她文学创作的养分,造就了今日的作家朵拉。

2023年,朵拉(一排左五)参加海外华文作家采风活动,图为她与众多海外作家在泉州弘一法师纪念馆前合影。
家庭对朵拉的影响还体现在她对文学创作的选择,因为父母对华文教育的重视,加之早期广泛接触华文文学,因此朵拉选择以华文来写作。从一开始写作的直白,到后来随着岁月的磨炼,朵拉的文学风格变得多样而丰富,她认为自己更倾向于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以细腻和深刻的描述去展现人性和生活的复杂,“虽然我的个人生活其实非常简单。”她笑道。
曾经,朵拉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就是将英文及马来文的作品,翻译成中文,“我想通过这种方式,为不同民族间的沟通做点事。”她自己的华文作品也被翻译成不同国家的语言出版,在她看来,不同语言之间有着不同的语言结构,还有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因此翻译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表达差异,“不过我觉得应该尊重翻译者的专业知识,他们肯定想把自己最好的译文呈现给读者,其实作品有机会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也是一种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