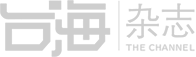百花村,在行政区划上,叫“长福村”。但十有八九者,只闻百花村,不知长福村。
六百多年前,1404年,朱熹后人朱茂林率领族人,一路南迁,当来到长福村时,看到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沟渠里流水潺潺,山坡上鲜花盛开,他们停住了脚步,从此定居下来,并世世代代以种花为生。
这一种就是几百年,花儿生生不息,尤以明清时期,花事一度兴盛。后虽经战乱摧残,长福村民种花的风气却没有随战火而湮灭。解放后,百花复苏,1963年,朱德委员长南巡视察,来到长福村,只见村中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花种草,置身怡人花香,他情不自禁发出了感叹:“真是个百花村啊!”从此,长福村,就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成了百花村,它的本名反倒被忘了,我也是这次再入百花村时,才知我叫了一二十年的百花村,实名为“长福村”。
67岁的朱江兴是我到长福村后见到的第一位本村人。实际上,我在多年前就已知他声名远播,当然,他的名声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传遍大江南北,这一年,他成了长福村第一个万元户,也是经媒体报道后万众瞩目的种花致富能手。从1997年起,他当了15年的长福村党支部书记,带领花农从庭院经济走上规模化种植和产销,一时间,百花村香遍全国。
可百花村在行政区划上还是叫长福村,于是大家就提议索性正式改名百花村。正式改名,就得经民政部门同意,而按当时百花村的知名度,朱江兴觉得民政部门十有八九会同意。正当朱江兴在大家呼吁声中信心满满准备申报改名的材料时,一个冷静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江兴啊,我们长福村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年年风调雨顺,花木茂盛,这都得益于祖宗取的名字——长福,长福。改不得啊!”朱江兴的父亲朱海憨,这位种了一辈子花的花工,阻止了儿子,“你当村支书是一时,当长福孝子孝孙才是一世啊!”
从此,没人再提改名的事儿。尽管没改名,但“百花村”,人们,无论远近,都叫它这名字。
“长福村”,续的是血缘;“百花村”,结的是花缘。

明代的塘北已是百花的村
百花村人于明代年间开始以种花为生,而到了清代,已是大规模种植,整个村子成了专业的花村。乾隆《龙溪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出郭南五里,有乡曰塘北,居人不种五谷,种花为业,花之利视谷胜之,盖地瘠,种谷不蕃,宜花故也。又能于盆中种古松及各花树枝干、扶藤,古致异常。”
志书中的“塘北”,指的就是长福村,这两个名字闽南话音是相似的,“塘北”叫久了就成了“长福”,“长福”又因为百花盛开而成了“百花村”。
我以为,塘北之所以演变为名闻遐迩的百花村,与它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塘北所在的漳州平原,位于九龙江流域。漳州在明清时期就十分注重水利建设,曾出了个把江南水乡治水经验娴熟应用到漳州流域治理的太守姜谅。塘北的“塘”字,及塘北所在的九湖镇里“湖”字,就都是历史上注重治水的烙印。而发达的水利工程,加上漳州平原肥沃的土壤,为塘北大规模种植花卉提供了可能。
塘北种花并不是为了观赏。当发展为产业时,花就一定要成为商品。塘北位于漳州府边上,而非偏僻山区,密集的人口为花这个商品提供了较为庞大且持续不断的消费群。塘北不成为百花村也难。
历史的积淀,使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花果苗农场、省花果外贸出口基地,显得水道渠成。那时候,农场和基地是按订单种植的。一般,省外贸部门都会在前一年年底,就定下今年需要哪些品种的花木用以输出,农场及之后的基地就组织花农根据所需种植,一般种植水仙花、榕树和铁树。
正是因为作为外贸出口的花卉基地,百花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资讯还很闭塞的时代,就引起高层的注意。比如,朱德于1963年南巡时,就专门来到百花村,见村子处处是花,便大赞“真是个百花村啊!”才有了百花村这个名字。
“文革”期间,百花村在一片“砸烂百花村”的叫嚣声中,百花凋蔽。

>>百花村内,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木养花。
一粒文竹种子复兴凋蔽花村
朱海憨是解放后百花村的第一代花农,因为种植技术高超,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位于鼓浪屿的华侨亚热带作物引种园请来当花工。和他一起被聘请的还有同村的两位花农。令朱海憨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之后百花村重振种花经济,竟发端于他从鼓浪屿采到的一粒文竹种子。
朱海憨在鼓浪屿当花工的那段时间,发现岛上不少别墅人家喜欢种文竹,而且花盆及四周常常落满文竹籽,“这就是种子,我父亲就跟文竹主人商量把文竹籽收集起来送给他,文竹主人也乐意,因为平日里他们也是把这些籽扫掉而已。”今天,朱海憨之子朱江兴在百花村的自家别墅里忆起了这段往事。
朱海憨把文竹籽带回家给了儿子们。朱江兴兄弟三人从父亲的手中接过花籽以后,就着手在自家花圃种植,很快成活,并一传十、十传百地种开了。文竹因长相优雅、文气十足,人们喜欢把它当盆景摆在客厅和书房,朱江兴家族的花圃里的文竹供不应求,文竹大卖为朱江兴家族花业兴起积累了第一桶金。1979年,朱江兴成了闻名全国的万元户。
文竹种植在百花村普及开来,村里的花农也都跟着种文竹,并从中受益匪浅,当茉莉花的售价一株不到二毛钱时,文竹的售价一株已两元。百花村很畅销的盆栽还有四季桔。无论是文竹还是四季桔,大都是运往厦门各大菜市场销售,厦门成了百花村最大的市场,百花村花农今天回忆起当年在厦门的销售盛况,这样说:“厦门像填不满的海!”可见,厦门对百花村的需求量有多大。
当时,百花村所在的九湖镇看准种花的商机,镇领导便在全镇积极引导种花种果,仅水仙花,全镇种植面积就有300亩,分属百花村等七个村庄。九湖镇还为此成立了九湖花木公司来推广花木销售,率先种花致富的朱江兴成了常务副总。一时间,在百花村的带动下,九湖花木远销全国各地。
1997年,组织上要求朱江兴出任长福村党支部书记,希望由他带头建设坚强有力的村党支部,并以此带动整个百花村的经济发展与民风改良。朱江兴连任三届有15年之久,直到2012年卸任。“如果要您总结这15年来对百花村的贡献,您会怎么说呢?”面对这个问题,朱江兴答:“贡献不敢说。但我做到了两点,一是带领长福村党支部连续8年获得龙海市五星级党支部;二是带领村民大规模种植花木,面积从原来的一千三百苗扩大到二万亩。”
尽管朱江兴已卸职五年了,但他在百花村依然有口皆碑,陪我采风的村委朱雪娥感叹道:“在历任村支书中,朱书记是贡献最大的。”她说,朱江兴出任支部书记前,长福村党支部三人五派,很不团结,是龙海市最落后的党支部之一;村民中也是山头林立,各不买账,甚至出现村落间打群架,严重影响了百花村经济的发展。而朱江兴出任后,全身心扑在村支部的建设和带领村民发展经济的事业上,个人经济发展都顾不上了。作为早期的种花致富能手,朱江兴早些时候就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一上任,就把他几年来积累的经验与资源全都用在了带领村民种植和销售上。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朱江兴就到荷兰学习参观,深受荷兰花木业产销分开理念的影响。在村支书任上,他便鼓励村民往外租地种植,而把自家在百花村占地很有限的花圃用作花卉市场。几年后,他又带着村民搭上漳州市建设百花长廊的好时机,在百花村口的国道线两侧建了一个又一个花市,真正从一个花村伸展出一个百花长廊。而今,走在长廊,就觉花香绵延不绝。
地球村时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百花村年轻一代甘愿埋首花丛、深耕花田吗?
“种花,赚不了大钱,但过日子容易,独立自主,不求他人,何乐而不为呢?”1972年出生的刘德隆说。
刘德隆从父辈手中接过小小的花圃,十几年用心耕耘,而今成了以出口为主的集团公司,花木销往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榕树、虎尾兰、发财树、仙人球等花木销量最好。
互联网和展会为这位百花村农家子弟嫁接起了与外界四通八达的销售网络。在德隆集团,有数十位大学毕业生每天都在通过网络与海外客户联络。“他们有不少是园艺专业毕业的,年轻,有冲劲,有想法,善于把实践与理念进行结合。”只读完初中的刘德隆深感大学毕业生的加盟使他如虎添翼。他们分属于贸易部、生产部、质检部、仓管部、采购部等部门,对德隆集团的销售部分贡献良多,“但种植方面,还是经验明显不足,需要我手把手教。”刘德隆坦言。
百花村还有不少如德隆公司那样走向海外市场的花木集团,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扎实的种植技术,有年轻人的加盟,有新理念的注入。这些愿意几年如一日深耕花田的年轻人,有不少是返乡青年,百花二代三代,他们从养花种草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如郑德隆所言“过日子容易”。
其实,早些时候,百花村农民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大学毕业后还回乡种花。“读好书,跳出农门”是很多当了父母的花农对子女的期待,即使如朱江兴这样老早就开眼界的人也是这么要求子女的。他的两个儿子和三个侄子都考军校,当军官了,只有一位侄子继承这个养花世家的衣钵。“但现在,我觉得当初的观念是落后的。”朱江兴而今回首总结道。
读好书又回到农门的,在百花村并不少数,这些返乡青年继承父辈种花手艺,又有新知识加持,种花卖花得心应手。
诗意盎然文脉绵长
与其他村子不一样的是,百花村活在许多文人的心里,尽管它现在实际上已是个商业气息浓厚、城镇化明显、不像村落的村落,但文人雅士忆起它,依然心头诗意升起,他们甚至常常把百花村诗化。有时,百花村又成为他们精神营养的所在。漳州是出文人的地方,而漳州文人,不管留下的还是离开的,他们的笔下大都有过百花村。
在百花村那些日子,行走于花间草径,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两位走得很远的龙海籍女诗人——子梵梅和安琪,而在其他村子时,我基本上不会想起她们,尽管二位都是我多年的好友。
诗人子梵梅离开龙海前在九湖中学教书。当学生时,她学的是根雕专业,所以,经常到百花村来。毕业后,她就留在九湖中学教语文,并为九湖写了许多诗歌。其间,她在校组织根雕兴趣小组,向学生传承根雕技艺,偶尔也会带学生到百花村来学艺。我未见百花村时,就经常听她说百花村,我对百花村的很多认识,都是从她的言谈中而来,并固化为美好印象。甚至她那衣袂飘飘的出尘之态,在我的心间,就是百花村的化身。
诗人安琪去北京前,就住在百花村边上的漳州。在诗歌界,她和百花村一样,都是漳州的名片。尽管去京多年,百花村依然是她魂牵梦绕的所在。在百花村采风的日子,当我微信告诉她时,几分钟后,她就写下了这首诗,我把它作为本文的结尾:
百花村
——给年月
她在故乡百花居住的某个村落
想起我——
这移居异乡的植物
是否水土不服
是否根系,还在不断蔓延,朝着南方的方向。
她用微信把她的问候传递给了我
仅此一念
便使干渴的灵感得到灌溉
她应该是月季月月有美意
而我是菊
随便放在哪里都能野蛮生长。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本文选自《乡关年月》,厦大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