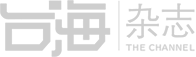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开始与柳涛打交道是在2014年年初,那年5月,台赛组委会首次组团赴台办展,作为第三届台赛台海环保科技新闻类金奖得主,柳涛也再受邀名单中。在第三届赛事中,除了《音乐与“闪电”》摘金外,他的《动物标本》、《孩们的冠军梦》、《温州动车事故一周年祭》也获得优胜奖。不过,那一年,柳涛因在北京有展览,遗憾缺席。那年是他真正从事新闻摄影的第10个年头,那一年他还在体制内当摄影部主任。
为了生计,一些本来很有天赋的摄影师把相机放进了摄影包,去做别的事了,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在2015年,反而选择做自由新闻纪实摄影师,对此,他回应说,“我也想能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毕竟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但如果前提是让我放下相机,我做不到。”
摄影对他来说,既是精神又是物质,更是在生活中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或爱或恨,或喜或忧。军人出身的他,对人满怀热诚,干活毫不惜力,以一个摄影记者的本能,静静地注视着人间一切的悲欢离合,讲述那些普通人所遭遇的不普通的命运。
柳涛格外珍惜在路上拍照的时间,每次的拍摄任务,他都会在家先做好功课,规划好时间和行程,为节省开支,柳涛在外地拍摄,住最廉价的旅馆,吃稀饭或面条。他也尝试做了一年的自媒体,后来发现,想要收入好,就要像机器人一样不停地去拍照,不管拍得好不好,只要新奇,吸引眼球就行,这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也不是他想要的。

>>2019年9月11日,哈尔滨,一名游客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参观。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在这里建立了一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这里同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称为世界两大灭绝人寰的杀人魔窟。
“我脱离单位,就是不想为了迎合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机构而拍照。我只想拍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小人物小故事,当它真实地出现在这个时代里,我会用相机忠实地去记录。”柳涛是一位感性的摄影师,擅长以饱含深情的照片讲述这些令人扼腕与唏嘘的故事,让那些与我们生活本无交集的人们,通过照片,走到我们面前,直接和我们对话,或是对视。对此,他直言,摄影师没有眼泪,观众也不会有眼泪。在摄影的路上,柳涛也曾跌过跟头。2005年5月9日,柳涛在雨中的厦门街头苦苦等候了一两个小时,拍摄了一组雨中骑车人路遇马路陷阱摔跤的图片,照片极具现场感和冲击力。这组照片让名不见经传的柳涛瞬间卷入翻天覆地的是非评论之中,一时间,各方争鸣,毁誉参半。也是这一跤让柳涛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路,才有了影像从心、摄影至善的信仰。
在摄影的道路上,尤金·史密斯对柳涛的影响较大,柳涛崇尚尤金·史密斯浪漫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也喜欢尤金·史密斯的图片故事。如果喜欢,就会在一个领域至死方休,柳涛只专注在新闻纪实摄影领域,喜欢朴实无华,杂乱有序,情感丰富的照片,这些年来,他通过报道摄影帮助过很多人,也改变过一些事,这让他很欣慰也很自豪。
要是没有成家,柳涛可能会是一名流浪摄影师,因为“无所顾忌,才更专注,我还有很多私欲,所以拍得还不够好。”
近年来,他一直在摸索和尝试纪实电影和直接电影。不过,如今,在业界算功成名就的他,却越来越不爱说话,他苦笑着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焦虑症困扰他多年了,他也少听歌,只听乐曲,只听能让自己放松的、安神的曲子。
所有灵感得到真正激活
《台海》:今年这个年想必让您印象深刻吧。有没有拍到自己满意的照片?
柳涛:我没有满意的照片,只有喜欢的照片。我的老家在湖北监利县,位于江汉平原腹地,距武汉205公里,不近也不远。坦率地说,今年回老家就没想要多拍照片,我连电脑和相机的充电器都没带。目的是回来看看老人,呆几天就走。没想到,被疫情隔离在湖北监利2个多月了。
新冠疫情是全球焦点,我生活在疫区,我们全家14人,就有7个武汉人,我本人也是从武汉回到老家的,没想到病毒离我如此之近。在疫区之中拍照,几乎都是下意识进行。当然,我也通过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和腾讯新闻,发个几篇稿子,传递了疫区的信息和希望。
《台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是怎样的一个契机?
柳涛:有20多年了吧。我哥哥有一台老式单反相机,刚开始我只是把它当玩具玩,什么也不懂。2000年,我在厦门南洋学院当辅导员。学校知道我会玩相机,就给我一台傻瓜相机,任务是拍摄学校的会议和各种活动。刚开始,还是有压力的,怕拍不好,被学校领导批评。自己买了很多摄影书籍学习,就这样慢慢喜欢上了摄影。
《台海》:将其作为职业,又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柳涛:最初我只是想做个业余风光摄影师,我还是蛮喜欢高校校园生活的。后来发现,新闻摄影更适合自己,更喜欢拍图片故事,但学校的工作时间并不允许我花更长时间去拍照。2004年,看到卢广的荷赛获奖作品《艾滋病村》后,对我的触动很大。后来,我辞掉学校辅导员的工作,去《东南快报》当一名实习摄影记者。从此,踏上新闻摄影职业道路,至今已经16年。

柳涛:我本来很享受报社的摄影记者这份工作,确实也干得不错。但传统媒体内外部环境一直在恶化,2015年,我被迫离开了传统媒体,成了自由新闻纪实摄影师。因为十多年的职业习惯,我很难有心思尝试别的工作或者另一种商业形式的摄影。
作为自由新闻纪实摄影师,优势在时间和选题上,没有任何的干扰,所有灵感也能够得到真正激活。劣势在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从2014年开始,我患上了焦虑症,至今还没完全断药。好在有家人和一些媒体的支持,目前也没有固定收入,主要靠稿费和公益摄影项目基金支持。
自由新闻纪实摄影师,这是一个说多了都是泪的职业。
《台海》:焦虑症是不是夜晚都睡不着?怎么调节?是否考虑用镜头记录焦虑症?
柳涛:焦虑症和抑郁症是至亲。失眠是病症,容易复发。主要靠药物治疗和自我心理治疗。我不会考虑用镜头记录焦虑症,那样只会加重我的病情。
注入爱的照片才有呐喊声
《台海》:这些年为了摄影,您走南闯北,到处拍照,一天天创作热情源自哪里?
柳涛:热爱,对新闻纪实摄影的热爱。10多年的记者职业生涯,让我看清想清了很多事物的本质,即便我现在不是体制内的媒体记者,但这并不影响我以职业记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很乐见因为我的照片对他人和社会带来的积极的变化。
《台海》:到外地拍专题,有没有哪次经历让您印象深刻?我对您拍的《濒危的古长城》 印象很深刻。
柳涛:我在内蒙阿拉善拍摄《大漠深处》时,体会到了人类在自然界的渺小。我在拍摄《濒危的古长城》时,看到城墙上的那些古老文字和图案,飘摇在荒芜的无人区,我心生敬畏。在拍摄纪录片《问石》时,我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山体震撼了,感觉自己的每个毛孔都流淌着热血……
《台海》:是什么令你孜孜以求、不断按下快门?
柳涛:因为新闻纪实摄影还有被需要的价值。我理解的摄影,不仅仅只是按下快门,更是关乎生命的哲学。
新闻纪实摄影完完全全地改变了我。它打开了我的人生,让我能看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如何生活,富人、穷人、好人、坏人,我所拍到的对象给予我一切,他们教育了我。




《湖北“无疫村”的坚守》节选
柳涛:前提要清楚,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如果你只是以拍照为目的,那么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张照片。摄影师没有眼泪,观众也不会有眼泪。
《台海》:可否谈谈摄影路上,那些让您流下眼泪的经历?
柳涛: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很感性的摄影师。每一次的快门声,就是一次感动。特别是参与汶川大地震报道时,我几乎是边哭边拍,现场控制不住情绪,甚至忘了自己新闻摄影师的身份。还有像《24名被拐卖的孩子》、《濒危的古长城》、《细菌战幸存者》,拍摄这样故事都让我心酸。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说,一张好照片它能让人看到摄影师注入的爱,因为只有注入爱的照片,才能有呐喊声,才能响彻云霄。
《台海》:在摄影的路上,您曾摔过跤,百度上还有一个关于您的词条。如今回看这些年遇到的挫折,您最大的感受、体会是什么?
柳涛:你说的是“水坑事件”吧。对我而言,那是一次深刻的职业教育,不是一次挫折。2005年以前,我对新闻纪实摄影的理解还没有很深的概念。2005年以后,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路,才有了影像从心、摄影至善的信仰。任何挫折,都挡不住我前行的脚步。
《台海》: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还会这样去拍吗?
柳涛:这是没有结果、只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真的倒流,我还是会,我能做的就是拍照。
一直崇拜体育的拼搏精神
《台海》:在您看来,什么叫新闻纪实摄影?
柳涛:新闻摄影本身就是纪实摄影,纪实摄影可以不是新闻。
《台海》:那摄影到底是什么?能做些什么?
柳涛:这是一个伪问题。一千个摄影师,就有一千个答案。很多摄影师认为,好的照片就是“一图胜千言”,前题是这张照片不需要用千言万语来解释。
摄影只是摄影,什么也不是,但藏着无形力量。照相机不会说谎,但它可以是制造谎言的绝佳工具,照片也就变成“照骗”。
《台海》:拍摄时,会不会担心视线会受制于镜框,而错过些什么吗?
柳涛:这是个摄影技巧问题。对摄影师来说,学会观察是最基础技能。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在任何环境,都有预见性,能轻松驾驭和把控现场。


《大漠深处》节选
1.2015年7月2日,内蒙腾格里沙漠的一个牧民。
2.2015年7月2日,内蒙腾格里沙漠,在修建沙漠公路的工人。
柳涛:过去在报社工作有这样的职业习惯,拍照时会为图片编辑留空间。现在我的供稿平台发生变化了,不再考虑平面大小,很多忧虑得到释放。
《台海》:您是如何描述您自己的作品风格的?
柳涛:我不关心自己的照片是哪种风格,只在合适的时候安静地按下快门。之前认为好的照片,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不是那么好;之前认为不好的照片,过一段时间又发现还好。
风格是永远都由观众来评。我只专注在新闻纪实摄影领域,我喜欢朴实无华,杂乱有序,情感丰富的照片。
《台海》:假使照片会说话,时间愈久,照片说的话愈多。在您的众多作品中,哪个作品让您一直有很深的触动?
柳涛:《睡在训练场的孩子》。这是2015年在福州体校拍摄的一张照片。也是当年因为时间差,错过荷赛调底的照片。我一直崇拜体育的拼搏精神,每次拍摄体育赛事或走进体育馆,自己的斗志就会被再次激发,这让我很受教。
《台海》:职业摄影和业余摄影的界限是否还清晰地存在?
柳涛:服务于某个机构或者独立的个人工作室的职业摄影师,他们有固定的资金链,生活上有保障;业余摄影师,以爱好而摄影,享受摄影带来的喜悦和快感。我都不属于这三种类型。我是专注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的自由摄影师。相机已经成为我的身体器官,摄影已经成为身体里的血液,拍照不仅仅只为生存需要,还是我的信仰。
《台海》:近年也满多摄影师或创作者尝试编导式摄影,对这类型的摄影作品有什么想法?
柳涛:我很少去关注别人用什么方式去摄影,也没资格去发表什么评论。摄影只是摄影,没那么重要,只要不违背道德底线,想怎么玩都行,一个摄影师远没一个医生重要。




《大漠深处》节选
《台海》:导演是您的另一个身份,当时是怎么想到转型?
柳涛:被逼的呗。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跳槽的人。如果喜欢,我会在一个领域至死方休。我也不认为现在是在转型,我定位自己是在升级。从静态向动态升级。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导演,至少现在不是。因为不管是摄影还是摄像,我都在严格遵循以纪实为宗旨,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导演是我的虚名,只是摄像工序上要有导演这样的称呼。目前,我还没接触除了纪实影像以外的其它商业和艺术影像。
《台海》:未来会考虑其它商业和艺术影像吗?
柳涛:未来可能会尝试商业和艺术片,但前提是必须把现在要做的事做好了,先把路走踏实了,再顺其自然。
《台海》:拍照片拍视频,完全两个思维。谈谈这其中的区别。
柳涛:拍视频要比拍照顾及更多,往往需要团队合作。一个人想要完成好一个有质量视频佳作,确实要克服很多困难,但不是没有可能。当然,也不是说拍照就只是按快门那么容易。
《台海》:近年来,您一直在摸索和尝试纪实电影和直接电影?
柳涛:纪实电影《辛巳劫难》,是我花了两年多时间,在日本东京、湖南常德以及哈尔滨和浙江等地,陆续拍摄完成的院线纪录片。

>>2019年1月1日,中国焦作,陈家沟村一位老人在教孩子练习太极拳。陈家沟村是中国太极拳发祥地,陈家沟也因太极拳而享誉全世界。
影片讲述的是,1941年11月发生在湖南常德的细菌战。当年日本731部队在常德地区,投下鼠疫病毒,致使鼠疫在常德地区流行长达4年,造成大量人员染疫死亡。当年参与对日诉讼的61名常德籍原告大多相继去世。目前,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仅有18人在世,其中多数疾病缠身,长期卧床。随着老人们的离去,关于细菌战的记忆逐渐消逝,但70多年前的那场劫难不应被人遗忘。目前该片正在后期制作中,计划在今年的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前后上映。
说心里话,一个自由新闻纪实摄影师,从静态影像到动态影像,我还能走到今天,已经超出我自己的想象。这其中的心酸只有自己能体会。还是那句话,我从事了一个说多了都是泪的职业。总之,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再艰难,也要向初心奔发。
《台海》:有团队与您一起拍摄《辛巳劫难》吗?
柳涛:没有拍摄团队,就我一个人。自己通过借钱和透支信用卡完成的拍摄。本来开始是有个人投资合作,合同都签了,后来还是违约了。接下来影片的后期制作费和发行,将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解决。
《辛巳劫难》是一部纯纪实摄影手法拍摄的电影纪录片。当然对于票房,也做好了心理准备,观众需要娱乐,商业片有自己的逻辑。但票房不是我们纪实电影最大的追求。相比那些看完后转瞬被遗忘的片子,纪实电影会像一种“慢性药”,可能某一天就在你的人生中起反应。我觉得纪录片和商业片要比的是,人们能从影片中收获什么。
纪实电影现在还很小众,在国外兴起较早,但是小众在中国其实已经是特别大众的事情。近几年,国内有不少纪实电影的口碑和票房都不错,以后可能更多。
无论是纪实摄影还是纪实电影,我想我改变不了太多现实,但是通过纪实影像,能让看到这些片子的人,因内心有感触而做出一些改变,这我觉得我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