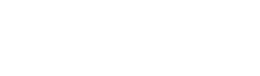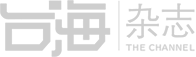夜来香
文/《台海》杂志主编 年月
母亲河九龙江一直流淌在我的生命里,每当闭上眼睛,我脑海里时常浮现那江面点点渔火、那江边簇簇灯光,耳旁回响的是船桨划过江面的欸乃声。
九龙江流入海之前的那一段,叫锦江。锦江两岸,此岸叫石码,彼岸叫紫泥。石码历史上是千年古埠,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龙海的县城。到报社前,我就在这里工作。
许多个下班后的傍晚,我都会穿过九二0路的骑楼,直奔锦江道。锦江道,听名字便知是锦江岸边的道,那儿一排大排档正沿江排开,说是“大排档”,其实是小桌子、小凳子、小海鲜。
关键是小海鲜,就因为有小海鲜,小桌子、小凳子,它们,就不再是简单的桌椅,而成为夜宴的担当。
暮色四合之际,白天躲起来的排档,沿江一字排开。母亲河喊我回家吃饭了,同样听到招呼声的,还有三两朋友。我们聚一起,吃海鲜、喝啤酒、吹海风、听水声、观渔火还有谈文学,也聊家常,偶尔骂人,把白天受的气,一股脑儿倒出来。
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因为“点亮夜经济”封面故事,专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城市管理系副教授徐国城时,他说:“经历了白天繁忙的工作,人们需要在夜晚‘蓄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夜间休闲给许多人带来了幸福感,夜晚放松身心,能够让一个人更加精力充沛、有创造力地投入第二天的工作中。”这话便让我想起了锦江道排档的一个个夜晚。那时,我还不懂得“夜经济”这个词,但今天回想,那时,我和我的朋友们,已是“夜经济”的受益者。美餐是其次,关键是蓄电,是精神层面的续航。
采访中,另一位专家,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先生,其高见也让我心悦诚服,他说:“发展‘夜经济’,当然不能只瞄准外地游客,而是要首先满足本地居民的文化和消费需求。本地居民不仅是主力消费者,也是地域文化的承载者、表现者。脱离了本地居民来谈城市精神、文化特色,无异于缘木求鱼。”
作为当年石码的本地居民,我们不就是“主力消费者,也是地域文化的承载者、表现者”吗?就是在那一个个夜食、夜娱、夜谈的晚上,我望着九龙江滔滔而去的江水,更加坚定了,走遍三江多省,去对诞生于故乡的“龙江颂”追本溯源,从而有了拙作《龙江人寻找龙江颂》。而在我离开故乡,到报社工作多年后,家乡的父母官希望我能回去再为家乡写作《乡关年月》时,虽然,这时,我因为现职在身,已无法全身心回到家乡,要完成近20个村庄的驻村采访,只能利用几乎所有周末和节假日,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那一刻,我似乎又听到了母亲河的召唤了。我离开了,但母亲河的灯火一直在我的心底亮着,这或许与那些年,锦江排档的夜夜蓄电分不开吧。
夜间休闲给人带来的幸福感,确实远超白天。夜晚的放松,让人脱去盔甲,人与人的距离也因此拉近。在两岸形势趋于严竣的这些日子,我时常回想起那十年甜蜜期与台湾朋友的交流互动,虽然这十年里的交流大事,我几乎无一错过,但脑子里不经意跳出的更多的是日常生活,而且夜色为底的画面不断闪现。在泰雅族居住的拉拉山,我们夜访民宿,月下敲门,惊醒宿鸟。在澎湖列岛的吉贝屿,我们放孔明灯,写下祝语,遥寄嫦娥。在惊涛骇浪中的绿岛,我们绕过曾关押柏杨李敖的监狱墙根,去寻觅在夜色中出没的梅花鹿。在台南赤崁楼的星空下草坪上,我们和台南文学馆的文友,一起吟唱胡德夫的《乡愁四韵》……
台湾的“夜经济”由来已久,两岸恢复往来,尤其是后来的“黄金十年”,更让宝岛的夜经济烧得旺旺的。但再旺的夜经济,失去了人潮,断了人的交流,也会忽明忽暗的。拉拉山的民宿,宿鸟常常睡过头吧?吉贝屿的孔明灯,嫦娥是否还能等到她期待的祝福?
犹记写作《乡关年月》期间,有多位两岸摄影家支持我,和我一起去驻村采访,2017年底,和我一起去石码采访的是台湾摄影家黄子明先生。结束每天高强度采访拍摄后,夜幕降临时,龙海市文联副主席、摄影发烧友蔡明辉,请我们去锦江边的骑楼吃小吃,其中一道猫仔粥,有鱼片、有海蛎、有鱿鱼,全是猫爱吃的,故名“猫仔粥”,每碗10元,黄老师特别喜欢,比我请他吃大鱼大肉更开心。特别要指出的是,蔡明辉先生便是我当年在石码锦江道的“吃友”,所以,我们吃“猫仔粥”时,配了很多话,全是旧人佳话。边吃粥边话仙时,骑楼里传来了邓丽君的歌声:“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歌唱……”
前几天,蔡大哥问我:“黄老师什么时候再来吃‘猫仔粥’呢?”
说的是吃,牵挂的还是人。